人文通史 早期雅利安人入侵南亚次大
印度的古典文明是从早期吠陀文明[Vedas Civilization]发展而来,而吠陀文明则是雅利安人[Aryans]创造的。雅利安人是一个侵入的民族,他们最初来到印度次大陆的时间大概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或许在这个估计年代之后约200年,一些宗教颂诗开始被收编成集,结果就编成了《梨俱吠陀》[Rig Veda],该诗集的最后编成大约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我们关于这一最早时期里印度境内雅利安人的知识,主要得自这一着作。《梨俱吠陀》展现出关于当时情形的相当清晰的画面:一系列有亲缘关系的部落,主要定居在旁遮普及其邻近地区,使用共同的语言,信仰共同的宗教,自称为“雅利安”(arya-)。据说,他们与许多被称作“达萨”(Dasa)或“达休”(Dasyu)的敌对民族处于持久的战斗状态。从有关这些战斗的多处材料表明,战斗结果是雅利安人大获全胜。在后来的《吠陀本集》和《梵书》[Brahmanas]等典籍描述的时期里,可以看到雅利安人主要是向东方扩张领土,一直到达恒河流域;而关于与达萨作战的记述则很少。象“蔑戾车”和“尼沙德”等其他名称,被用来称呼非雅利安人部落,而“达萨”则成为通用的“'奴隶”一词。另一方面,“雅利安”这一名称不仅与外部的野蛮人相对立,而且与四种姓中最低的首陀罗相对立。在后一种场合,“雅利亚”自然就得到“高贵的”、“尊敬的”之义。这个词的这两个含义一直沿用到古典时期。北印度被称为“雅利亚伐尔塔”(Arya-varta)--“雅利安人居住的国土”,或巴利文的“雅利安·阿雅塔南”(ariyam ayatanam)。耆那教经典也经常提到雅利亚和蔑戾车之间的差别;在泰米尔文献中,北印度的国王是指雅利安人的国王。另一方面,佛教的“八正道”(ariyam atthangikam maggam)是这个词用于道德伦理意义的例证。在这里,这个词毫无种族的意义。
雅利安人(其出现于印度西北部已为《梨俱吠陀》所证实)从印度次大陆之外,通过一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连续多次的迁徙,到达了他们当时占领的地区。这一迁徙的最后阶段距《梨俱吠陀》开始编成的时间不可能相去太远,但同时也必定过去了一段足够的时间,人们对迁徙的清晰回忆已经消失,因为那些诗歌中没有关于这一事件的确切资料。雅利安人之入侵印度,没有书面文献的记载,人们也未能从考古发掘中发现它的踪迹,但是,以比较语言学为依据,它仍被确凿地认定为一件历史事实。印欧语系起源于欧洲,吠陀形式的梵语就是这一语系最古老的语言之一。要将一 种属于这个语系的语言从远道带往印度,唯一可能的途径是说该种语言的民族的迁徙。以有关语言的相互关系为依据,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一过程的概况。
除了在总体上属于印欧语系,梵语即古印度-雅利安语与伊朗语族也有着较为密切而特殊的关系。伊朗语族中最古老的代表是古波斯语和阿吠斯塔语。实际上,古代印度-雅利安语和伊朗语族语言的关系十分密切,因而这两个都自称雅利安人的民族在更早的时期里必定曾经是同一个民族,讲着同一种语言(尽管适当许可方言之间的差异)。这一通常被当作原始印度-伊朗语的早期雅利安语,是后来的伊朗语和印度-雅利安语得以衍生出来的语源。在雅利安人侵入印度以前的时期里,他们很可能居住在中亚地区,以奥克苏斯河[阿姆河]、锡尔河、咸海和里海为界。可以假定,雅利安人的各个分支就是从这个基地推进到阿富汗高原,然后从这个基地下降到旁遮普平原。从这同一地区,另一些雅利安部落朝着相反的方向,西向移入伊朗。在那里,他们第一次出现在亚述记载中是在公元前9世纪中叶。一般认为,他们开始占领伊朗不早于公元前1000年。如果上述估计的时间是正确的,那么雅利安人占领伊朗的时间就比其迁入印度晚得多。伊朗人保留了对其最初的家乡的记忆,称之为“雅利安人故乡”。这一地区一直为伊朗人所占领,到突厥人侵入时为止。
雅利安人在他们早先的家园开创的共同文化和宗教,仍然分别反映在伊朗人和印度-雅利安人最早的典籍中。在后者的文献中,查拉图士特拉[查拉图士特拉(Zarathustra)意为“骆驼的驾驭者”,即古波斯语的琐罗亚德斯,古波斯的宗教改革者。]的宗教改革带来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改变,其结果例如,原有的单词“神”(梵语为deva-)获得了“魔鬼”(阿吠斯塔语为daeva-)的词义。同时,吠陀经中某些重要的神(如因陀罗),在阿吠斯塔中则被降到魔鬼的地位。尽管如此,仍有相当数量的共同遗产保留下来:虽然因陀罗这个名称变为指魔鬼,但其称号“杀弗栗多者”(Vrtrahan-)的伊朗语形式Vrthragna仍指一尊重要的神祗 ;与吠陀经中的密多罗(Mitra,婆罗门教、印度教神名。《吠陀》中的昼神)相应的伊朗的密斯拉(Mithra,古代波斯神话中的光与真理之神,后成为太阳神),仍为他们最重要的神祗之一,后来在罗马帝国有过一番不寻常的经历;崇拜火和苏摩祭是印度和伊朗两者的共同遗产;吠陀中的毗伐斯万特之子耶摩[Yama,太阳神毗伐斯万特(ViVansvant)之子,死者之王]和阿吠斯塔中毗伐赫万特之子伊玛[Yima,伊朗古代神话中也为太阳神之子,人类始祖]这样一些人物也说明有一种共同的神话。印度和伊朗还有着共同的基本宗教术语,例如,吠陀中的“霍塔尔”(hotar),意为“祭司”,“雅吉纳”(yajna)意为“献祭”,“利塔”(rta-)为“真理、神规”,在阿吠斯塔中分别为“扎奥塔尔”(Zaotar)、“雅斯纳”(yasna)、“阿夏”(asa-)(古波斯文为“阿尔塔”(arta-)。同样,共有的专门名词也出现在政治(“统治权”,梵文中为ksatra-。阿吠斯塔文为x'sathra-),军事(“军队”,梵文为sena,阿吠斯塔文为haena,古波斯文为haina)以及经济(“田野”梵文为ksetra-、“可耕地”urvara-,阿吠斯塔文“家园”为So1thra,“庄稼”uruara)等领域中。在印度,社会阶级的划分具体表现为四种姓制度,这与伊朗的情况极为相似。可以认为,这一共同继承的文化,在其后期各阶段,是雅利安人在中亚的故地演进的。他们在向印度迁徙之前,可能在那里居留了相当长一个时期,有证据表明,在更早的时期,雅利安人的住地还在更远的西方。首先,雅利安语言与印欧语系的联系表明,雅利安语源出于欧洲,人们由此必然假定,是更早的一次移民将它们从欧洲带往中亚。其次,芬兰-乌戈尔语中有外来的雅利安语这一现象,为雅利安人更早的故乡还在更远的西方提供了饶有兴味的证据。例证之一是芬兰单词sata“一百”,看来可以在语音上相当于'Sate-(即这个单词的印度-雅利安语和原始印度-伊朗语的形式,而不是后来的伊朗语sata-)。有相当多类似的外来词不可能源出于伊朗语,因而它们必定是在原始印度-伊朗语时期被接受过来的。因此,在这一借用语汇的时期,雅利安人和芬兰-乌戈尔人的祖先必定有过密切接触。考虑到芬兰-乌戈尔语在目前的分布状况,及它们在古代所处的大致位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些词汇被借用的时期,其语言被借用的原始雅利安人居住的地区不会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山脉以东。只是在对于芬兰-乌戈尔人有所影响的这个时期之后,雅利安人的主要中心才移往中亚。
在暂定为将近公元前2千纪初的这个阶段,雅利安人已被看作一个单独的社团,业已脱离了印度-欧罗巴人的其他分支。在更早的阶段,大约是公元前3千纪的中期,人们可以假定这样一种情形:使用派生出后来雅利安语的语言的人们仍是原先的印度-欧罗巴社团的成员,他们的语言是印欧语的一种方言,尚未发展成为单独的语族。这一发展是在上文指出的那个阶段(公元前2000一前1500年)中完成的。这假定暗示:雅利安人原先的住地还在更远的西方。对此,也能提出语言学上的证据。在所有的印欧语系语言中,有迹象表明,波罗的-斯拉夫语族与印度-伊朗语族有着最密切的关系。由于这些语言不可能远离它们初次得到历史性证实的地区,这一联系就可用来指出印度-伊朗语族最早的发源地。
除了许多其他特有的类似之处,这两个语族都具有早期颔音化的特征(梵文的Saturn和阿吠斯塔文的Saturn“一百”,与拉丁文的Centum相对照,即为例证),这种情况在阿尔巴尼亚语和亚美尼亚语中也可见到。由于这一共有的革新,通常认为这些语言形成了印欧语系中一个特殊的语族,并按阿吠斯塔语中“一百”这个词,将它们称作“萨塔姆”(Satem)语族。事实上,看来很可能是:这一变化发生的时间很早,因而使用所有这些语言的人的祖先在那时候都还互有接触。除了这些特殊关系以外,还有证据表明,印度-伊朗语与希腊语也有特殊的关系,这在动词的构词法上尤其明显可见。
没有迹象表明印度-伊朗语和其他印欧语言有特殊的联系。就西印欧语言(意大利语、凯尔特语、日耳曼语)来说,鉴于它们的地理位置,不可能有这种联系。赫梯语和小亚细亚的同源的语言处于一种特殊地位,由于它们与人们熟悉的印欧语形态差异很大,因而需要假定,它们很早就分离出去了。这些民族翻越巴尔干山脉进入小亚细亚的时间必定比他们最初出现在书面历史记载中要早得多。更有疑问的是关于两种习惯上称之为吐火罗语甲和吐火罗语乙、相互有密切联系的语言的情况。本世纪初,使用这两种语言的写本残卷在中国新疆出土。鉴于这些残卷的位置,人们希望它们会显示出与印度-伊朗语有较密切接触的一些迹象,然而,从这些残卷却找不出这方面的任何痕迹。更有甚者,从它们也看不到与印欧语的其他分支有什么特殊的联系。对于这些事实,最好的解释是,假定使用这一语言的人群分离出去的时间很早(尽管不如赫梯人等的分离那么早)。必定是上文概括的雅利安部落后来向东的扩张将他们推向越来越远的东方,直到最后定居在中国新疆。从语言上找不出这两种人早期接触的痕迹,只有到很晚的时期,伊朗人对吐火罗人的影响才显露出来。
迄今为止,我们都只能完全根据语言上的关系去解释雅利安人的起源和早期迁徙。关于公元前约1500年以后的活动,则有了可供使用的文件证据。这些资料并非出于雅利安人永久定居的国度--印度和伊朗,而是来自近东,雅利安人的一支在那里建立的一块不具持久影响的短期领地。出自这一地区的文件证据包括若干专门名称,一些神的名字和一些单词,从这些词汇可以推断出公元前1500-前1300年间雅利安人曾出现在这一地区。他们的出现总是与胡里人[Hurrians]有关,胡里人是土生土长的非印欧人,当时也正在大事扩张。尤其是胡里特人的国家米坦尼[Mitanni],从其国王的名字推断,在其最有影响的时期,系处在由雅利安贵族支持的雅利安国王统治之下。另一些位于叙利亚的小国的统治者也有类似的雅利安人的名字。
这些雅利安人的人数不足以将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明强加于他们所定居的国度,他们似乎总是将胡里特语作为他们的官方语言。在这一时期结束后,他们被土着居民同化,没有留下更多的踪迹。最重要的文件是赫梯和米坦尼君主之间的一份条约,其中载有4个在吠陀经中常见的神祗名称:即因陀罗、伐楼拿、密多罗和纳萨蒂亚[双马童],此外,出现在喀西特人文件中的意为太阳神的苏利亚(在其他方面,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喀西特人与雅利安人之间的联系),和在赫梯人文件中得到证实的火神阿耆尼,看来都是他们从雅利安人那里借用来的。在米坦尼人基库里用赫梯语写成的一篇关于驯马的论文中,包括了一些雅利安语的专门名词和一系列雅利安语的数字。另一些雅利安语的单词,在与胡里人有关的文件中也时有出现。
人们讨论较多的问题是:近东的雅利安人是与雅利安人的印度一雅利安人分支、还是与其伊朗人分支有更为密切的联系,或者,近东的雅利安人是否相当于分离前的原始雅利安人。目前流行的看法是,他们可能与印度-雅利安人分支有联系。这一结论部分地是基于语言方面的考虑(例如,单词“一”aika-,与梵语的eka-相符合,而与伊朗语aiva-不一致),但也基于这一事实,即上述诸神是吠陀经中特有的神,而在伊朗语中,这些神中仅有密多罗作为神出现;至于原始雅利安人,除了密多罗,它们之中任何一个在这一阶段是否能被看作是神,尚有疑问。
假如近东的雅利安人可能与印度-雅利安人有着特殊的联系,就可以得出一些颇有兴味的结论。首先,我们必然断定,在印度一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或伊朗人前去占领伊朗之前,雅利安人使已分为两个分支。其次,我们必然断定,在迁往印度之前,原始印度-雅利安人使已占据了伊朗东北部。鉴于雅利安人出现在近东的时间与一般认为的雅利安人移入印度的时间大致相合,因此他们都是出自同一基地,即后来被伊朗人接收的领土--伊朗东北部。
在扩张的顶峰时期,雅利安人占得的领土比所有其他印欧人加在一起所占据的还要大得多。甚至在他们大规模迁徙、从而占领印度和伊朗之前,居住地仅限于欧亚草原之时,他们所分布的区域就远远大于其他印欧人占有的土地。为了解释后来的大扩张,我们必须假定有利的气候及其他条件造成了人口的持续增长。只有基于此说,我们才能解释他们何以能够在伊朗和印度北部这样的大片地区殖民。正如已经述及的,雅利安文明特有的面貌,就是在这个时期-公元前1500年以前的几个世纪-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在最早的印度和伊朗文献中发现的,就是这一文化。也正是这一文化,由于两种传统之间的极大相似性,必须被视为共有的遗产。我们在《梨俱吠陀》中发现的这一文化,不是在印度成长起来的,而就其最基本的成分而言,是从外部引入的现成文化。
应该提到的一个常见的错误观念,是由于对“雅利安”这一术语使用不当而引起的。这一名称只能专门适用于印度-伊朗人,因为这是他们用以称呼自己的名字。不应该象过于频繁出现的那样,将其推而广之,泛指印欧人。这样滥用的结果是往往将早期难利安人和原始印欧人混为一谈。结果,雅利安人亦即印度-伊朗人在向印度等地迁徙之前,也就是在一个虽未特别指定,但无疑是公元前约1500年以前相当长时期中的居住地俄罗斯草原和中亚草原,常常被当作是最早的印欧人的故乡。其后果是,希腊人、赫梯人等等被说成是从这片当时只由印欧人的雅利安人分支占据着的地区移民出去的。正相反,有材料证明,印欧族的欧罗巴各个分支是欧洲的土着居民,雅利安人是在从他们分离出来后才向东扩展的。正如已经论及的那样,在这一时期,也就是在他们与其他印欧人分离和后来开始于公元前约1500年的迁徒之间的时期里,他们文明的特有面貌才发展起来。
人们注意到,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看来是在吠陀诗篇编成大约相当长时间以前发生的,因为在吠陀诗篇中找不到关于这一迁徒的清晰回忆。另一方面,这些诗篇却频繁提到雅利安人与以前的居民达萨或达休的斗争,占领他们的土地,缴获他们的财物,至于这些被迫离乡背井或被征服的民族之身份,主要的,也是最可能的看法是,他们就是印度河文明的创造者。这一在最初被发现时大大出人意料的文明,必定早于吠陀时期,但对于它的衰落是否由入侵的雅利安人造成,或者说,从印度河文明的终结到雅利安人的出现,是否经过了一段时间,尚存有一些争论。吠陀经典本身的证明材料无疑是支持前一种观点,这明显地表现在它经常提到摧毁城市,战神因陀罗被认为是“破坏城堡者”,火神阿耆尼也被突出地提到其这一能力。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许多印度河流域的城市似乎都是毁于火焚。考虑到这些反复出现的材料,似乎不免得出这一结论:印度河流域城市的毁灭是雅利安人之所为。
实物遗迹清楚表明,在某些方面,印度河文明要比雅利安文明优越。尤其是,印度河文明是一个高度发展型态的城市文明,而相形之下,雅利安人则并不熟悉城市生活。雅利安人的优势在于军事领域,在这方面,他们使用马拉双轮轻便战车发挥了显着作用。他们取得胜利的后果是几乎完全放弃了城市,这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便终止了罗马一不列颠的城市生活,差不多如出一辙。雅利安人不仅对利用他们所征服的城市不感兴趣,而且进缺乏管理城市的专门能力。在吠陀时代的大部分时期内。雅利安人用木材建造住所,他们以村落而不是以城市为单位散居各地。他们的房屋和家具由于主要用木材及其他易腐烂的材料造成,因而保留下来可供考古学家记录的为数不多。直到最近,印度的吠陀时期在考古方面几乎仍是一片空白。甚至现在,这种状况也没有多大进展。只是到吠陀时期之末,城市的发展才重新开始。对印度河文明,考古学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来源,而关于吹陀时期难和安人的资料则完全要依靠以口头方式相传下来的文学典籍。这些典籍没有提供任何专门的历史记载(因为那不是它们关切之所在),而是提供了大量的关于某一历史性或半历史性人物之出现的非主要的材料,也描绘出那个时期生活和文明的一幅相当清晰而连贯的画面。
一个讨论较多的问题是,印度河文明对雅利安文明具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各种看法大相歧异。总的说来,吠陀经典本身给人的印象是,这种影响即使有,也无关宏旨。首先,吠陀诗人对达萨及其文明持一种不妥协的敌视态度,在宗教方面明显地不接受任何影响,要不然在这方面可能会产生一些结果。此外,经考古学证实的印度河流域大多数城市的毁灭和人口的减少,必然有效地消除了大多数可以传播这种影响的基地。当然,到了后来,当雅利安文明发展成为印度教文明时,许多非雅利安的影响出现了,但这些影响在吠陀时期并不明显,而且看来与印度河流域城市的史前文明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根据《黎俱吠陀》中提到的河流名称,能够确定雅利安人在《黎俱吠陀》时期占据的领土。这些河流首先是印度河及其主要支流,旁遮普的5条河。由此向西,提到了格鲁姆河(Krumu)、戈马蒂河(Gomati)和库帕河(Kubha)(即今日的古勒姆河、戈马尔河和喀布尔河)以及苏伐斯杜河(Suvastu)即斯瓦特河,表明雅利安人扩展到了今天的阿富汗境内。向东,萨拉斯瓦蒂河(Sarasvati)、德里萨德瓦蒂河(Drsadvati)和阎牟那河在雅利安人领土内,恒河是在一首较晚的颂诗中提到的。这片地区的大部分都在印度河文明的范围以内。另一方面,《梨俱吠陀》却不大提到印度河下游地区,在那里,印度河文明也同样繁荣过。
雅利安人分为很多个独立的部落,正常情况下由王(Rajan)统治。这些王在不对达萨或达休作战时,便经常相互征战。然而,基于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生活方式,雅利安人高度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种族整体,并且意识到他们与早期土着居民之间的悬殊差别。那些原有的居民,一部分以首陀罗的资格被吸收人雅别安人社会,一部分则撤退到雅利安人暂时未到达的地区。雅利安人在一片前此人口稠密、高度开化的国土上得以保有他们的特性,并如此完整地保持自己的文化这一事实,说明了他们不是通过一场征服战争,而是在持续时间很长的一次又一次迁徙浪潮中大批而至,足以提供为数众多的居民,转过来又能形成进一步扩张的基础。当时在近东盛行的情况恰恰相反。在那里,小股武士实现的征服,结果是只建立起暂时的统治,但他们的人数太少,数代之后便不免被当地土着居民所同化。
在后期吠陀经典描述的时期里,雅利安人占领的地区继续扩大,重心也向东转移。到了《梵书》[Brahmanas]时代,雅和安文明的中心地带是俱卢人和潘查拉人的国度,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北方邦。与此同时,位于旁遮普的西部拓居地则退居次要。进一步向东扩张已在进行,在这个地区中最重要的国家有侨萨罗、迦尸和毗迪诃。雅利安人在这一时期的主要进展是沿恒河而下,基本上保持在这条河以北。迁徒的主要路线可能是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丘陵地带前进,首先是避开河流附近森林密布的地区。在这一时期的典籍提到的部落和王国中,位于恒河以北的最多。恒河以南的则非常少,例如切迪人Cedis、萨特万特人(Satvants)和维达尔巴(Vidarbha)王国,提到它们的次数也很少。这时,雅利安人的周围是各种各样的非雅利安人的部落,《爱达罗氏梵书》中列举了这些部落的名称:安陀罗人(Andhras)、奔那人(Pundras)、穆蒂巴人(Mutibas)、普林陀人(Pulindas)和沙巴拉人(Sabaras)。从这些资料看来,鸯伽国和摩揭陀国还只是部分地雅利安化了。
《梨俱吠陀》对于雅利安人和达休之间的战斗作了突出的描绘。正如我们所知,这反映了一场持久的武装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雅利安人最终成为毫无疑义的战胜者。在后期的吹陀文献中已不再提到这些,用以指非雅利安民族的“达休”这一术语,也较为罕见了。另一方面,用以称呼原始的森林居民的“尼沙德”这一术语则较为频繁地出现。对此的解释是,雅利安人的推进和殖民的性质已有所变化。一旦印度河文明倾覆,其大部分领上被占领,就不存在任何有先进文明的国家与雅利安人抗衡了。这时候,恒河流域似乎稀疏地居住着森林部落,它们不具有先进的文明,不能对雅利安人作出一致的抵抗。沿恒河流域而下的殖民开拓起初主要是在河流北岸,大体上是清除森林、建立农业拓居地等事项,这是一个持续好几个世纪的进程。在未被开发的森林地区,原始的“尼沙德”部落继续居住在雅利安领土的内地。看来,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容忍的基础上的。随着森林清除活动的进行,森林部落独立存在的范围自然日益受到限制,他们中的一部分以普克萨(Pukkasa)与旃荼罗Candala这样的名称将自己依附于雅利安人社会的边缘,构成那些终于成为受压抑等级的核心部分。
雅利安人占领印度的第三阶段是在公元前800一前550年这一时期。根据。《梵书》中的材料,我们注意到在这一时期之初,雅利安人占领印度的地段仍然比较有限。在他们周围,环居着非雅利安民族,其中有的民族的名字已经提到过。将近公元前6世纪末,我们可以看到,在佛教和耆那教兴起之时,雅利安语言和文化已在大得多的范围内广为传布。
显然,其中间有一个广泛迁移和殖民开拓的时期。结果是,“雅利亚伐尔塔”--雅利安人的国土--的疆界有了确定:北抵喜马拉雅山,南达文底亚山,东、西濒临大洋。此时的主要扩张路线之一位于西南方,它包括了阿槃底及其附近地区,并远至戈达瓦里河上游地区的阿湿波卡(Asmaka)和穆拉卡(Mulaka)。雅利安人继续向东推进,占领了孟加拉大部分地区(奔那、苏马、文加等等)和奥里萨(羯陵伽)。
在《梵书》时期,雅利安人基本上保持了其种族特征及其吠陀文化。雅利安人社会内部有相当的发展,尤其是婆罗门的地位提高,组织增强了。礼仪也大大增多。我们赖以窥见这一时期情景的典籍,主要就是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国家组织稳定而发展,各种官职已有记载,尽管其确切职责不尽清楚。政治机构日益庞大,国家开始取代部落。文献和考古学都证实,物质文化有了相当的进步。城市生活再度小规模地开始,因为提到的若干地方,如加姆比利耶(Kampilya)、帕里卡克拉(Paricakra),阿桑迪瓦特(Asandivant)。看上去已是城镇而不是乡村了。
公元前800一前550年这一时期中的迅速扩张带来了这样的后果:在新区,雅利安人的分布比在老区稀疏得多,他们与原有居民混合的程度也高得多。这一事实在一些古代典籍中有记录。例如《波迭衍那法经》中说,阿槃底、鸯伽、摩揭陀、苏刺陀、达克辛那巴塔、乌巴弗利特(Upavrt)、信度和索维腊等地的人都是混杂的血统,并进一步规定为那些去阿拉塔人、加勒斯格勒人、奔那人、索维腊人、文加人、羯陵伽人和普拉努纳人国土的人们赎罪的供品。这份名单包括公元前800一前550年期间殖民开拓领地中的一大部分,并且证实,这些地区只得到不完全的雅利安化,与早期发生的情况形成对照。名单中还包括一些非雅利安人部落的名称,其中许多无疑仍保留了原有特征和语言。
或许应该认为,前雅利安人对雅利安文化的影响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发生的,而且这种影响与由吠陀文明到后来的印度教文明的过渡有联系。后来到《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时发展到顶点的史诗传统大概也于这一时间开始形成。
宗教的新发展也在这一时期初现端倪,它最终演化成为后来的印度教,在许多方面与吠陀的宗教迥然有别。成为以后印度教文明特征的种姓制度[Varnas],在这时由于大量形形色色的先前独立的部落必须以某种方式加入雅利安社会结构而大大增加了其复杂性,这些遍布于新征服领土许多地区的部落必定构成了全体居民中的大多数。以吠陀文化为基础的雅利安文化仍然是构成中心的因素,但自此以后,它便更加受到非雅利安的影响。最晚感受雅利安文明影响的是在南方达罗毗荼人的地区。在锡兰,最早的雅利安人的殖民据信大约发生在佛陀时期,最初的雅利安人向南印度的渗透可能在同一时间内出现。后来,孔雀帝国控制了德干的大部分地区,只有最南方的泰米尔诸王公保持着独立。其后的萨达瓦哈纳帝国也体现了雅利安人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和渗透,可作依据的事实是,这一王朝及其后紧接着的一些王朝,均以中古印度-雅利安语为官方语言。这一政治影响与来自北印度的宗教传播--婆罗门教和佛教或耆那教的传播--是有联系的。然而,与以前的扩张阶段比较起来,雅利安语言并未永久地被强加于这一地区。约公元500年之后,坎纳达语和后来的泰卢固语开始用于碑铭。土着的达罗毗荼因素逐渐占了上风,雅利安印度和达罗毗荼印度之间的疆界恢复到标志着公元前500年前后雅利安征服极限的那条界线上。与此同时,整个次大陆由一种共同的文化联合到一起。雅利安人是这一共同文化的初创者,而达罗毗荼人和其他民族也作出了他们的贡献。恒河以南与这两条前进路线相连的地区也都逐步被纳入雅利安人的统治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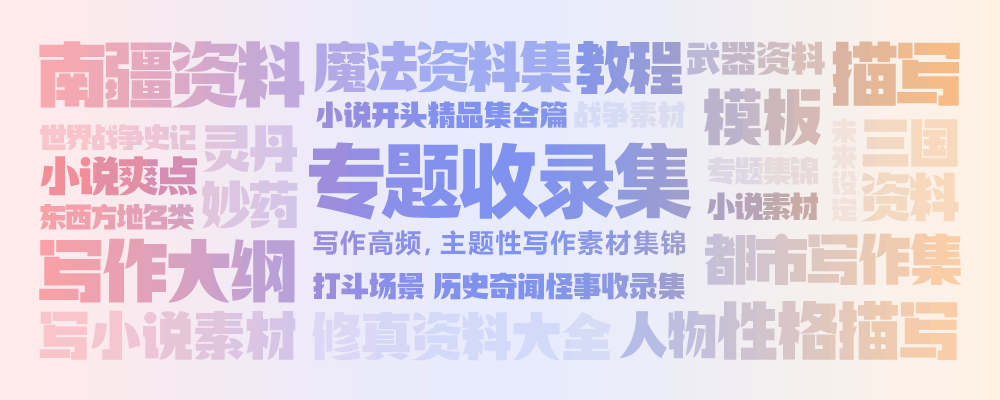






















 滇公网安备 53032302000118号
滇公网安备 53032302000118号 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